有两个故事。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我认识的一位大学哲学教授,他在圈内颇有名气,也写过一些哲学普及作品。在微信刚刚诞生的前几年,他说微信非常侵占人的时间,所以他卸载了微信,拒绝阅读公众号。而后还专门写了一封抵制微信的公开信,此事在当年曾轰动一时。两年后,我又碰到了这位教授。我问:“你现在还不用微信吗?”他很骄傲地说是,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部几乎消失的诺基亚键盘机:“我现在最多就用这个东西,绝不上网,绝不用智能手机。”

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我乘高铁去上海出差的时候。在检票口,一对夫妻正焦急地和检票员沟通,女人嗓门特别大,脸涨得通红,看上去要哭出来了。这对夫妻拖着两个略显破旧的旅行包,黝黑的肤色模糊了他们真实的年龄,后面排队的旅客显得有些不耐烦,检票员冷冷地说道:“没有健康码进不去的。”
原来,这对农民夫妻没有智能手机,也就没有健康码,检票员不让他们上车。
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那位教授朋友。我不禁担心如果在疫情时期他仍坚持自己的立场,拒绝用智能手机,那么他现在寸步难行。哲学家的骄傲有可能被一个小小的健康码彻底击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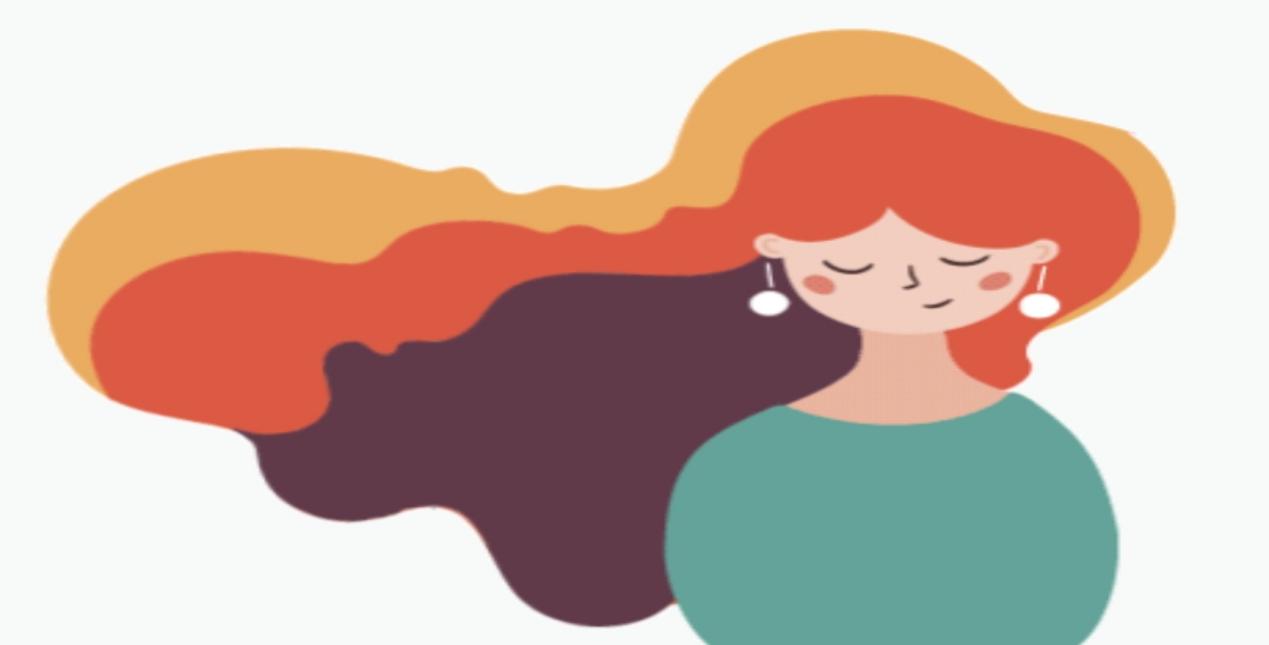
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今天的人类,这对农民夫妇和哲学教授,好像被看不见的海浪困在一座岛上,成了同一类人。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群体,“科技边缘人”或许是贴切的。
在媒介语境下,“边缘群体”指的是因经济结构、文化基础等被主流排斥的群体。除了那对农民夫妻,还有山区的孩童、家中的老人,他们中的大部分被动地成为“科技边缘人”,只能蜷缩在科技之光照不到的阴影中,最后掉进时代的裂缝中。他们渴望拥抱,但没得选择。
而另一个极端是,哲学教授主动把自己边缘化的行为,更像是一种归隐。他如此排斥现代科技,其实是在思考人文主义和商业主义关系的过程中产生了纠结与挣扎。
但作为一位具有人文精神的现代隐士,他有选择的权利。他可以出世,也可以入世;他可以拒绝智能手机,结果是得不到一个健康码。他也可以拥抱科技的变化,在残酷的商业竞争的底层发现人文精神的善良和悲悯。
科技生命体以指数型发展的形态,改变了速度、时间和距离的意义,让一切都变得激烈、快速和廉价。所以科技边缘人痛苦的根源在于,在科技迅速解构世界的过程中,科技自身尚未达到成熟的形态,现实和精神却都在滞后发展。

对于哲学教授而言,信息智能社会带来了新的哲学思辨。人文主义是从农耕文明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,它与现代的商业主义,特别是金融资本主义和科技资本主义有着天然的冲突。然而200多年来,人文主义在和商业主义的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,我们还来不及用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去解释商业主义,这让隐士们感到陌生和不适应。于是,他们用抵触乃至抵制,来表达这种不适。
其实那天在高铁站,令我难过的是,有人说了这么一句:“瞧,那个没有绿码的人。”
所以“科技边缘人”的出现,既是科技本身未到成熟形态的缩影,也是我们对当今人文、商业和制度关系的深刻反思。
(文章转载自意林杂志网)